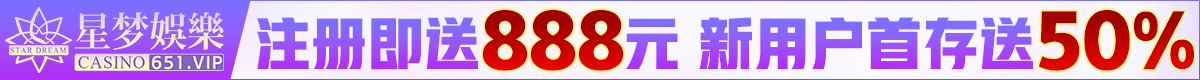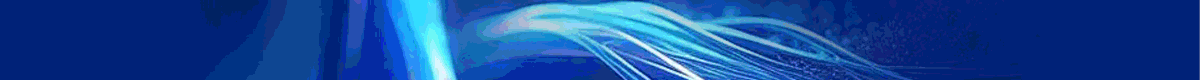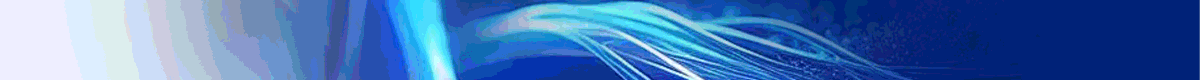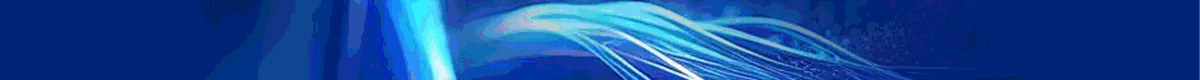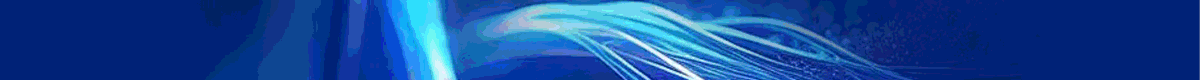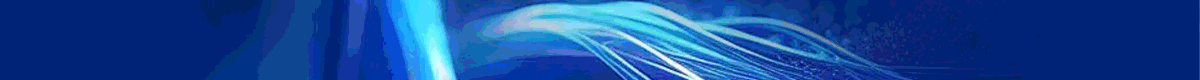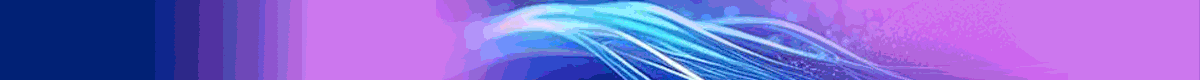密诱 第十六卷 · 第四章 猎取人头
猎取人头,就是初先将其本人不满现实的情绪作为前提。当然,要猎取眼下有名的刀根靖之的人头并非是件容易之事,要想完成此项工作,必须在没有他人的干涉下进行。
“为什么要关心父亲的事?”
“那是因为,”
我平静地说道:“我们好像感觉到了你父亲被什么国家注意到了。”
“那怎么办!”
“不要担心,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只是要他的脑袋。”
“这不是更吓人啦。”
亚矢子拍打着我的膝盖。
“抽时间还是回一趟家里,暗中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如果只是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的正式招聘,我们这些第三者的猜测就不会有错了。我总感到在刀根教授的周围有一股势力在活动,并造成了一种危机。”
只字不提抢夺钻石之事,危机其实就指的是它。
“明白了。近期将找一个时间回家一趟。奸吧,今晚我们不谈父亲的事了吧。”
计程车已到了代官山的公寓。
亚矢子先下车,我紧跟在她后面。从后面开来的车擦过身旁,很快朝坡山驶去。
那辆深蓝色的车压着左侧车线行驶,冲到坡上顶点时在视线中消失了。
尽管闪过的时间很短,还是看到了那开车的是一位年轻女子,那张脸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特别是在附近碰上这位开车女子就更觉奇怪。
代官山是一座带欧洲色调红砖修筑的公寓。
赔偿费足种高级商品。大学助教的工资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在付出大额赔偿费的背后有亚矢子的父亲刀根出力。
两人挨紧着走进入口。
乘电梯到了四楼。
是四0 一号房间。刚一推开房门,很窄的专门用来脱鞋的地毯上发出一股铁锈臭味,上面有些湿润。
一边是白色的墙壁的尽头安放着一面横着的大镜子,就像杜鲁门总统的房间那样。紧紧被我搂住腋下的亚矢子映照在镜子里。
镜中的亚矢子朝我微笑。
外面响起一阵风声。
亚矢子仰起脸,开始用一种特有的眼光看着我。我相信,她在这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刻发出的这种光芒是所有男人都抵挡不住的,我感到自己被一点点地吞噬,我的情感和意志已逐渐被消融。一种巨大的灼热的情感将他包容,随即点燃了人的五脏六腑,我低下了头,像进入了无限的水中。
“天荒,要我!”
她柔情地说。
我感到她已用了一生的时光准备了一次自焚。我看着她。
“要我!”
她的声音中注入了全部的心血,那神情中有着一股催人泪下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似乎一切不可更改。我不再言语,开始温柔而深情地抚摸她,吻她,我用嘴、用身体、用情爱、用哀怨、用追忆……用人类应有尽有的心绪和动作调动她的感觉。
亚矢子感到我的嘴从她的脖子滑下去,在她蓓蕾般的乳头上停了一会儿,又滑向她的小腹,他的那双特解风情的手与嘴配合得那般天然相独到,我的大手盖住她的最隐密处。继而我的嘴带着巨大的毁灭,游丝般的呻吟开始峰回路转而锋芒微露。随着我的动作和情感的加剧,那呻吟开始混成一股激流,很快爆发出来。
我已被亚矢子的呻吟融化,我不知自己到达了绝望的巅峰还是极度欢乐的巅峰。
对我而言,绝望相极度的欢乐总是连在一起的,我曾经在这种巅峰之上行走了上千次。
我急风骤雨般的大动起来,想用男人的身体和情欲摧毁她们,我似乎巳厌倦了一切,包括所谓的爱和恨。
亚矢子感到她被带上的雪峰之巅,继而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烈火熊熊的火球。
只几分钟,她感到一阵大雨猛烈倾泻下来,她的身体在火与水的交融中剧烈的冒着烟,这种疼痛把她的身体弄成了破碎的片断。
亚矢子尖厉地叫起来,当她明白她拚命地挣扎也是徒劳时,她不再动。任我把她捣碎的身体——抛入漆黑绝望的深渊。
舞台的灯光变暗,幕布徐徐降下。
响起了一阵掌声,表演结束了。
刀根靖之望着帷幕仿佛依依不舍地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出通道。他今年已满六十三岁,脸上露出聪颖的表情。尽管满头银发,可温和的举止中他依然像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在闭幕之后观众响起经久不息的喝彩声中,刀根用蔑视的眼神望着这些急性和失礼的动作。
看芭蕾舞很疲劳,也许是上了年纪吧,至少从他的外表看来是这样。法国芭蕾舞团在日本公演时,刀根没缺任何一场,特别是那些舞姿又富有古典芭蕾的高度动作的优美姿势简直是他忘掉了研究和对工作的不满。
不过,他还是常常比其他人先走出来,因为他讨厌闭幕时观众爆发出的喧闹声。
推开沉重的隔音门,来到剧场大厅,他发现一位脸熟的男人小跑步地过来。
男人穿这一件没开口的衬衫,胸前熟识的证章闪闪发光。
他是河岛泰介的秘书北见。此刻正用眼神暗示,然后同走向出口处的刀根一言不发、肩并肩地走出去。
“外面有车等你。”
在东京山野公园树丛中的暗处,化化会馆大厅的外面,水银灯的光线下停着一辆黑色的日本高级轿车。
北见单也打开车门躬下腰。
“请。那位女性陪同你。”
“那,你呢?”
“我随后就到。”
“河岛没有来?”
“是的,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由谷端来陪同。”
刀根靖之正欲钻进后排座位,顷刻间屏住了呼吸。
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后面的座位上。金发大眼,皮肤白净,用含情脉脉的眼光朝他微笑:“请,请坐吧。”
讲的是流利的日语。
自从六年前失去妻子以后,刀根在那狭窄的空间里几乎没有过跟女性这样同坐在一起的经历。尽管研究室的职员里也有女性打字员,但从没有感到有异性吸引。
轿车启动了。下了坡就进入山野的繁华街道,经广小路朝未广町、神田方向疾驶。
开车的是一位从不开口的男人。
“法国芭蕾怎么样?”
“不错。比起英国皇家芭蕾舞和美国华盛顿芭蕾舞来,更具有一种高超的格调。当然,像日本的牧阿佐和具谷八百子著名的舞蹈家也相当不错。但日本的男芭蕾演员身
密诱 第十六卷 · 第五章 莫斯科
材都显得有些不健美。”
“我也有同感。日本的芭蕾舞,特别是女舞蹈家的水准达到了世界级别,而男性就显得有些跟不上,真是遗憾。”
“你的名字?”
“叫夏米。请多多关照。”
刀根喃喃自语,倾斜着脸想着,她好像同什么人有些相似,对,想起来了,那是在很久前,在西伯利亚曾有一面之交的某女军人的面容。
那女军医的名字不是知道叫什么吗?米夏、马夏、拉夏、不管怎么叫,后面总带夏的发音。在那令人生厌的收容所里,只有那女军医既亲切又漂亮。
“谷端在什么地方等?”
“是在成城学园的家里。”
“你是在日本长大的?”
“不,只呆了两年时间。在日俗文化协会里工作。”
“老家在什么地方?”
“哈巴罗夫斯库。”
哈巴罗夫斯库……一点也没印象了。
要是不问就好啦,刀根有些后悔了。
从神田至崛端外的阴暗角落,到处都挂着西伯利亚的雪花,他不怎么喜欢雪。
眼下极力结束那些记不清的回忆。
高级轿车一点声音也没有,悄悄地穿过夜中的大街,从三宅饭店经赤阪又出青山街,好像是朝世谷方向。出发之前,听说过成城学园,因此刀根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志忑不安。一般大使馆、谍报机关老窝和秘密机关的总部都设在宁静的住宅区。
“先生,可以抽一支烟吗?”
米夏抽出香烟。刀根接过香烟轻轻送到口边。
米夏用白细的手送过火来。
今晚,或许肯定要答应吧?那前来接头的谷端千三的后面肯定是河岛泰介。
也许他们抱着某种政治上的投机来正式邀请吧。总而言之,今晚一定要把条件、待遇、研究设施的内容、期限和对方的关心程度谈个透彻。
轿车没多久就进入了成城学园的大街。住宅区内十分安静。汽车发出的引擎声微弱得同衣服的摩擦声相似。
穿过一排很长的围墙,到了一处官邸。
看门牌也许就知道是谷端的家,然而门灯照耀下的门牌上是女性的名字,叫敦贺由希子。
简直忘了。
汽车滑进正门的停车处。
米夏先下车,然后推开门。
“请,大家都等着你。”
这是装饰堂皇的房子,整个屋顶是铜的,洋房却显得古色苍然,冕形灯照亮了几间房屋,房屋十分宽敞。地上铺了高级地毯,圆形窗户把房子衬托得近乎充满神秘感。谷端在里面的客厅里等候。
“打搅教授真过意不去。”
以前是上级,眼下地位发生了变化。谷端早已是十足的商人了。
“谷端,希望你的谈话要简单明了。我打算坚持每天早晨的慢跑,所以晚上要早点休息。”
“明白教授的意思。请坐下谈吧。”
谷端指了一旁的沙发。
“彼此都知其性情,为了吃饭和喝酒没有什么拘泥,所以就选了这轻松的社交之地。”
“真让你费心了,我不适合酒宴,能不能到外面什么地方去谈?”
刀根总对这带神秘色彩的房子有些放心不下。
“是的,不过还有些话要解释一下。这里不会引起人的怀疑,而且今夜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智子小姐、米夏小姐、来见见咱们的同事。”
除了陪同来的米夏之外,还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走来做到谷端旁边。这位上身穿黑色毛衣,下身套着黑色裙子的女子长得十分漂亮。
她自我介绍,名叫秋吉智子,是十天前曾出现在北海道的鸿之舞,与多田直志驾驶双奥托飞机降落在殿场的女人。刀根当然也听说过此事。
智子和米夏把装有烈酒的瓶子放在桌上,做喝酒的准备。
侧旁有一人边喊着欢迎边来到眼前,脸上带着文雅的微笑,她是一位成年的日本女人。
谷端赶紧说:“我来介绍吧。这是本办事处的敦贺由希子。敦贺女士在青山是经营宝石和服装以及合法证券,是我的贸易伙伴,被誉为日本服饰、宝饰界中的女皇。”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敦贺由希子脖子上和胸口处有珠宝装饰,身上穿着漂亮的印花服装,笑容满面的坐在刀根身旁。
刀根心情越来越不好受,她习惯于在马场上那些发暗的、砖瓦结构的帝国航空宇宙研究所中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的生活,却看不惯这些奢侈无度的酒席,以及女人的肉感黥激,顿时,莫名的怒火使他难以保持平静。
“来,喝一杯。”
谷端端起酒杯:“怎么样,好像是在下决心把?”
刀根无语,视线对着这些女人。
“哎呀,你用不操什么心呀,在这里的人是决不会把秘密向外界露出去的。”
“是吗?”
他懒心无肠地嘟哝:“那太费心了。”
“教授的烦恼我十分理解。但是,教授在日本研究的鈇合金研究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有理?充其量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阶层知道这种材料可以制造飞机的主翼端,而对鈇在宇宙工学和航空力学中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了解。如果,先生还抱有对学问的良心和给予研究方面的热心的话……”
“尽管这样说,我还是日本人。是靠文部省的预算扶持起来的。让我暴露研究内容是……”
“是的,成功之处不正在那里吗?靠日本的官僚预算是发挥不了先生的能力。真是令人为之惋惜。学问常常是超越政治的。重重叠叠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错误忽视了先生,然而你的研究之花必定会结成巨大的硕果——”
“等等,请等等。”
刀根打断他那富有诗意的话题:“如果,我向那个V 先生讲出满意的答覆,具体的该怎么安排呢?”
“作为平常去的话,必须是莫斯科大学工学部会友教授。如果先生想参观更实际的实验装置,作为俄罗斯最得意的宇宙开发部门研究设施的负责人……”
“不,我听说的不是那样。如果决心已定,就可以做那样准备。是什么时候?答覆了再出发?”
“等回信少则也要一两天。出发的日子并不是要看天气如何,最迟不过一星期或者十天以内。假设顾虑到有各种不测之事的出现,当然最好越快越奸。”
“谷端,请梢等一下。”
刀根望着那有些发愣的表情:二星期或者十天?……太快了,难以置信。也请考虑一下我的立场,放心的是,身边的四个孩子已经成长为大人,都独立生活,夫人也过早去世。已过六十的身躯,还不知要寄放何方才能结束天涯孤独的余生。我的立场还是要回到日本。”
不完全像说的那样,刀根挂心的是谷端流露的出发不会受天气的左右。
飞机肯定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俄罗斯民间航空局的飞机尽管是性能优良的民航班机,但也不适应机场的气象条件。从今天谷端的话中,他感到的并不是平常的飞机。
是什么,刀根也从没看过。
“那位V 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介绍一下,往后我好交谈。”
“好吧。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
谷端言简意赅地说:“你想会见V 先生吗?”
“在日本能会见?”
“当然,如果你希望的话,现在我把他叫到这里来。”
“呵——”
刀根又一次惊讶不已。
“米夏,请把你父亲叫到这里来。”
谷端的声音十分平静。
“好,请稍后。”
米夏回答后就消失在里屋。
紧接着一阵短暂的沉默。
时间只持续了两三分钟。
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讲俄语的男中音大声地响起,米夏附和着呀啊呀啊的,并不断地摇手。刀根没想到一看见眼前的俄罗斯男人四肢就显得疲软了。
那男人穿的不是军装,是一套质料昂贵的西装。奸像也不年轻。那副象征政府高级官员聪明才智和眼睛边子闪着亮光,一位体格健壮、肌肉结实的俄罗斯老人立在那里。
谷端千三的声音对刀根来说又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
“也许还是介绍一下吧。这位是俄罗斯外国贸易部长尼柯拉斯。多布鲁依林先生。多布鲁依林先生为下月在东京举行的日俄经济协作委员会作会前的准备工作——教授,恐怕早把他忘了吧?”
“是吗?我们明白了。”
我放下电话。
多田直志回转头抱着胳膊:“什么?有了恋人吗?”
“没有。旅馆、代官山公寓相我的房间里都没有。”
我一口气地接着说:“亚矢子这东西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这伙海盗集团到东京已经是第三天了。在芝蒲埠头仓库里藏好酒桶之后,我在这里专心看守,并同多田直志分头与各企业和宝饰商秘密地接触,正当洽谈钻石抛售之事有了新的进展的时候,在他们身后有发生了令人费解的怪事。
首先是刀根亚矢子。本想问一下托亚矢子办的事情进行得怎样,可是一连打到好几个地方她都没有接电话。
“思,有危险。”
多田直志双手抱在胸前,焦虑地拧挤着眉头。这般神态不只是亚矢子的事,还涉及到酒井令子。她昨晚溜出爱情饭馆之后,便一点消息也没有。
黑天辉之领到了寻找酒井令子的任务。在另一台电话机旁,黑田抓住机子不放手,打听酒井令子工作时经常往来的地方。
“谢谢,谢谢。给你添了麻烦。”
他放下电话。
“没有。”
“制片厂里也没有。办公室的同伴们对忘掉时间表的事情正大发雷霆呢。”
根据黑田所说,酒井令子在昨天夜里九点左右跟他说有点事,就离开了饭馆,奸像是朝着自己的公寓所在地惠比寿去了。管理人员说层看见她在大门处进了电梯,以后再也没看见什么了。她的房间里十分安静,但夜里十一点时,隔壁的人听见酒井令子的哭声,看样子是刚坐车回来就被等候在屋里的人抓住,然后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样,这样一来……
不只是多田直志感到了危机,我也自言自语地嘟哝开了。我感到了一股危险向自己涌来。敌人并不只是开始反击,而且是手段残忍的反击。
对这些是早就有准备。自从那些卸在鄂霍次克海域处的钻石被掠夺之后,走私集团并不会含着手指、恬不知耻地在床上光哭。
我和多田直志对视着。沉默是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给予承认。为了打破屋内笼罩得抑郁气氛,我离开桌子,打冰箱取出了罐啤酒。
中午,明媚的阳光从窗外射进。外面大楼的窗子玻璃反射的阳光非常刺眼。
大楼和大楼之间斜跨着一条单轨道,那弯曲的轨道在人们的视线里剧烈的晃荡,叫人十分惧怕。酒井令子在到达东京的那天夜里,曾对我去亚矢子处的事很不满意,也许是心情浮躁才出饭店去散散心吧。
假如是这样的原因被敌人抓住的话,她未免太可怜了。
算了吧,别想这些了,反正只有两人,而且都是女人。如果真的给敌人抓住了,也不过是打击了我集团中最薄弱的力量。
“喂,天荒。”
多田直志换了一种口吻:“你知道刀根教授的家吗?”
“嗯,知道,不过从来没去过。”
“电话号码有吗?”
“应该有,请等等,我把它写在什么地方了?”
嗓子非常渴,我一口气喝干了一听啤酒。从内衣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啦啦啦啦地翻着。
“最好是准确的,然后马上打电话。”
多田直志的话都很明白。其一,确认出亚矢子是不是在那里住下了;其二,刀根教授自己还在不在那里。
密诱 第十六卷 · 第六章 现实意义
电话传出一位清晰的老年家庭女佣人的嗓音。
我告诉她自己是亚矢子的朋友,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主要是打听亚矢子回家没有。
山崎峰说:“呕,是小姐的——”
她像早就知道我的事似的,声音变得急促和亲切。
“不,我没有看见亚矢子。先生也从昨晚没有回来,我心里十分不安。”
我惊呆了,重要的当然是刀根的消息。
“刀根教授昨晚可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也不清楚。有人带口信说教授去看法国芭蕾舞,回研究所时在山野耽搁了一下。”
“他的话中没具体说是在什么地方?”
“对了,是一位男人的声音,我想一定是研究所的人。”
刀根教授一晚没有回家,我倒不是同情山崎峰的焦急之心,而是想到了刀根的生命安全。
“还是那么一回事?”
看我接电话的表情,多田直志哆嗦起来:“如果只是猎取人头,对方应该是采取较为体面的行动。从教授没有回到家中来看,多少是被欺骗了,交谈中不仅是要招聘的事议,而且还包藏着危险。”
“是的,我也这么想。”
我说话的时候楼梯有脚步声响起,朝仓匆忙地推开门,跑了进来。
“糟透了!货被劫走啦!”
“什么,被劫走了?”
“是的,货还没有到达山野车站。那列货车被强行开到大宫操车场接受检查。”
简直是祸下单行。以朝仓为首的四人今天一早就乘卡车赶到山野车站,任务是取回那列火车上的酒桶。
当时,在山野车站取货视窗出,朝仓受到莫名其妙的接待。根据办事人员的话说,有情报向国铁当局说,从网走发运的天荒的货物有爆炸物之疑,国铁要在大宫操车场接受铁道公安局官员的检查。发现三个酒桶是可以之物,存放在操车场之中不能领走。所有这些不管有任何理由都必须经过公安官员的调查之后方放行。
朝仓说:“简直吓了我一大跳。我想要是被带到铁道公安办公室太危险啦,于是就慌忙挣开办事员的手逃了出来。我这样做行吗?”
朝仓的选择看来是正确的。如果去找国铁部门发牢骚等于自掘坟墓。就是说,敌人会用木桶引出我们的人,然后先发制人——狗娘养的,我骂了一句。但是还认为利用货物列车是最可信赖的一步棋,没想到最先遇到了失败。这些家伙比伦敦的里库斯列大盗还高明,混入了官方机构,竟敢对享有信誉的国铁动手。
“遗憾啦,看样子没有什么办法想了。这样一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钻石。真是新兵还未上战场,身上就被打伤了。现在只剩下童贯幸平的海上偷运的部分和我们运来的部分。朝仓,你放弃货车那部分是明智的。”
对我的判断,多田直志也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
此时,桌上的电话响起。
我作出一副战斗的表情。
正是偏有凑巧。
刀根教授、亚矢子和酒井令子相继失踪之后,如果敌人同他们任何一人有接触的话,是完全有可能来电话了。
我看了看多田直志的脸,多田直志抓起电话跟对方说暗语。
“是,东京警备队——”
门的外部钉上了一层铁皮。
当然,是用来伪装临时办公室。
“天荒在哪里?”
电话机里响起嘶哑、粗野的声音。
“我就是,你是童贯幸平吧。”
啊,我发出一声惊叫。不是敌人,是盼望已久的童贯聿平的电话。
“什么!童贯幸平吗?真把人吓得坐立不安!”
“发生了什么事?声音简直象要同谁打架似的。发生了什么?”
“哎,请等等……”
“现在你在什么地方?已经离开了馆山吗?”
昨晚,曾打到童贯幸平的北斗丸渔船进入馆山港的电话。
因此,也把这间临时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给童贯聿平。
“不,没有打算那样做。我们还在馆山隐蔽,暂时没有出发。”
据童贯幸平报告,东京港里航行的船很多,为了安全在东芝蒲进港,码头的法规很严格,海上保安厅和水上署的监视哨也十分仔细。走私船肯定被作了记号,所以,昨晚就一直隐蔽在千叶县馆山附近的峡谷之中,以便于了解有关进港手续等,再寻找时机。看来危险仍然很大,在芝浦进港可能会被敌人察觉。当然,可以从内房、三浦半岛和伊豆附近的峡谷中进入,然后将货悄悄地卸下,也许这样比较安全可靠。
这只是一种商量,是一种建议。
童贯幸平表面有些粗野,其实是一位小心谨慎的人。
“如果按那些码头规定,刚一提出申报秘密,偷运的事就会暴露,我们反而会吃亏是吗?……请等一下。”
我用手按住听筒,同多田直志讲话。
其实不同多田直志商量,我也会觉得童贯幸平的建议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十分正确。自从刀根教授、亚矢子和酒井令子失掉消息以来,如果真的是敌人所为的话,那么芝蒲的仓库,或者童贯幸平等人也会被暴露出来了。
四月,一个闷热的夜晚。
马路里冒出一股烤鸡肉串的香味。艳丽无比的霓虹灯比那波光闪耀的海面有增无减。我借着灯光进入靠经国电御徒町车站的马路。
转过一间出售高尔夫球用具商店和中国饭店的转弯处,前面有一家主营进口货,其实是走私品的钟表商店。
店内的商品有用鳄鱼皮做的手提包、钱包、各类皮毛料、录影机产品、宝石和模型枪,这些商品占满了整个狭小的陈列窗。与其说是钟表店还不如称之为杂货店更恰当。
刚一推开门,埋在如山杂货中的一个男子抬起头大声喊道欢迎光临。
“老板在吗?”
我眼里带着一种亲切的目光扫视了店内。
“先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请转告,就说天荒来了。”
一个男人很快就从里面推开办公室的门进来。这人六十开外,那红光闪闪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少东家。让你久等了,快,请坐。”
“辰已先生,可别再称少东家哟。”
“说可以这么说,可这……”
这位年满六十岁的老人,穿一件很像出海人员穿的作业服,名叫辰已五郎。
他微躬着腰领我来到办公室,让给沙发坐,然后吩咐店堂伙计快端咖啡来。
“还是到附近的酒吧去喝吧。”
“哎呀,你这不是见外了吗?既然到了我这里还说这些话。”
“是吗?”
说话之前,辰已大量着我全身上下,然后接着说:“啊,想起来了。”
他盯住我的眼眶。
眼中流露出并非感到惊讶的神色。
我只是稍微耸了耸肩头,止住了继续想出口的话。本来事先说好的有事情可以用电话联系。让他帮忙推销巨额钻石,而辰已像是找到了买主,可电话里什么也没有说。
既然下了决心就得有胆量去干,这样才会使更大成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个地方如果拿出实物来的话,敌人会立即出现吗?
室内顷刻出现死一般的静寂。这种静寂或许是辰已感到对久未现身的我突然而到不知什么才奸?沉默之中带有某些叫人困惑的含义。
他可能是对我来这里所要做的事情感到震惊和担心。那两个个酒桶里装的全是钻石!这对常与黑社会打交道的辰已五郎,或是其他男人来说简直不敢相信,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有些神经病。
两大酒桶钻石,价值八百亿日元!总之看了实物一切就会真相大白的。
“看你脸上的表情,担心出手会带来危险吧。”
“不,少东家!没有什么,那样的事不要紧。你不是小孩啦,危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难道不是吗?”
“推销地方大致找到了吧?”
“不能让他们发现。现在他们正准备给予凶残的反击。因此,尽可能的加快时间将实物推销出去。”
“当然,靠辰已之力是有限的,还得找些帮手。如果国内推销受挫的话,还可以通过关系在香港和新加坡出售。当初我接到电话时还想到你那副孩子气的脸,心里好生担心受怕,心脏一个劲地剧烈跳动。”
我不是只让辰已充当据客,还考虑到他知道表面主管第一宝饰业务的谷端干三。
辰已在第一宝石饰初建开始直到今天仍同他有买卖交易,也许他还了解谷端背后的一些事情。
谷端的经历、人际关系,以至现在鲜为人知的工作。可他作为亲苏派的院外活动集团中的一员,肯定同秘密机关有什么勾当。在电话里曾提到这些事。如果谷端在某处有什么秘密办事处的话,那么它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失踪的三人会不会也被带到那里去了呢?
“还打听了一件事情。谷端千三是生意人,但也有不同之处,消息十分可靠。第一宝饰对待那些没有经验的同行跋扈,主要是依赖销售廉价钻石,当然他的背后是靠廉价收购走私的俄罗斯钻石。谷端看起来很象一个经验十足的商人,他的头脑清晰,商才横溢,思路纵横无际。这家伙擅长鞠躬行贿,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商人。早年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时候碰上钻石事件,为了将现金换成实物曾暗地里四处活动。这家伙的思维敏捷,要不然的话混不到现在这种地位。”
“喝,谷端也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思,这么说我的推测错了?”
“但,还是不能那么想。”
辰已立即答道:“的确,谷端千三是作为千岛桦太防卫军的一员派往真冈守备队,也曾在商会露过二、三次面。可是在俄罗斯占领之后,日本军的军官和下士官几乎全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那个谷端不会在装有商会资产的船上。而且,在那条船上也有我搭乘,可以证明船上没有谷端此人。”
“但,那三人原来是日本兵呀?”
“姓什么我忘了。从北海道一直随船行动,在东京分别后怎么也想不起那件事了。”
“哎,如果是当官的或者是什么的,当然会有些脸熟的吧。战后,在东京突然碰到一些熟人,当时日本正处于贫困时期,听没听说有四人为了糊口曾共谋袭击了商会的事?”
“是的,有那么回事。不过想不起来了。”
辰已脸上浮现出有些难为情的神色:“万一,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特别对我来说还不敢肯定。”
辰已不是那种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投机者。他挪进一步道:“要尽快查明河岛泰介和谷端千三的阴谋?并且在钻石被人夺回之前,想办法救出去向不明的三人。一我这下被他问住了,不容分说,关键就在这里。
“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自从接到少东家的电话之后,我也考虑了一些事。我认为还是最好去一赵成城学园。”
“成城学园?这是怎么回事?”
“谷端和河岛的秘密办事处可能就在成城那里。同行们都称那特有的铜顶洋房子为含羞草哩。”
取名为含羞草的洋房子?我自语时辰已打开桌子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像是什么会员证的卡片。
“这不是我的。出入里面的某经纪人是那里的会员,往往要参加一些活动。这张卡片是从那男人手里弄来的,请放心,拿它进去看看吧。”
“这是进入含羞草房子的通行证?”
辰已拿起身旁的体育报,手指在报纸艺术和技能下端的广告栏一角:“会议,恰奸在明天晚上召开。看,请看看这里吧。”
洋水仙盛开了。四月二十一日晚上九点恭候。含羞草夫人“那含羞草夫人指的是什么?”
“哦,我也是从这张会员证主人那里听说的。含羞草指的是一位叫敦贺由希子的女人,她是那房子的主人。”
“她的名字请给我再说一遍。”
辰已停顿一下后又说:“不,孩子。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事是常见的,即使那样也不要费心去注意它。“那个女人在青山经营服装,商店是一座大楼,挺气派地被称为服饰和宝饰界的女皇,还听说是谷端或者河岛泰介的情妇。她常常召集一些富翁来含羞草招待会。那些同河岛和谷端一起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同事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块。那里有一间容的下百来人的大厅,所以被称为百人出头露面的场所,为了有一天变成百万富翁,个个都对它抱有兴趣。这里不仅是思念西伯利亚时代的落难,还是宛如同情妇幽会的游乐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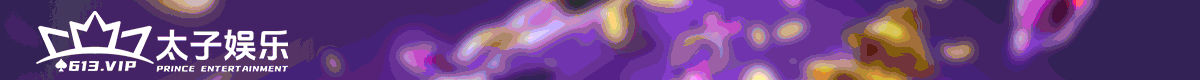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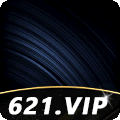






 星河电子
星河电子 星宇电子
星宇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