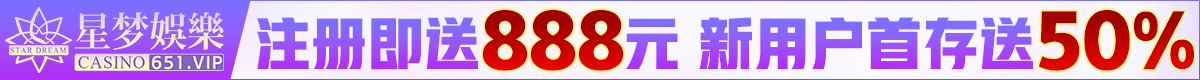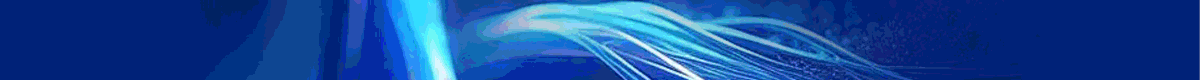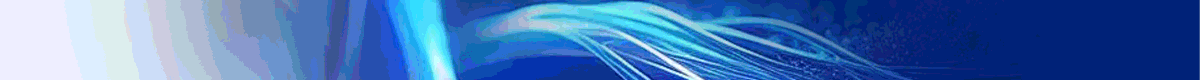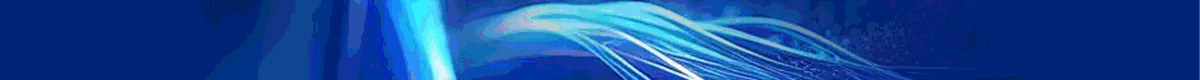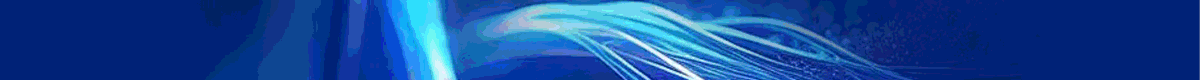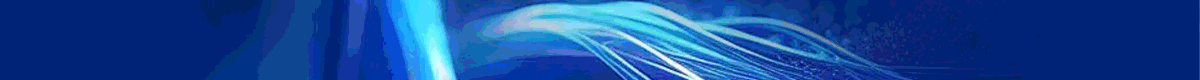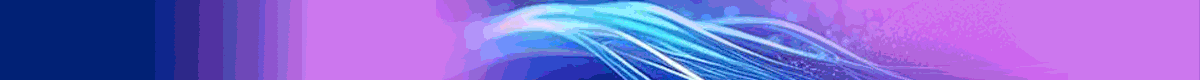第十七回柜中塌前淫雨绵绵
诗曰∶
杯酒伏干弋,弦歌有网罗。
英雄竟何在,热血洒青莎。
且说大郎也携了月儿回来寻欢,屋中二郎合菊儿先行躲起,大郎遂于二郎的床上,卸了衣裳上了月儿身上干事,乍合之际,觉道那月儿非处女身儿,遂恼,拨出尘柄之际,又听那床板下面通的一声响,道∶“啊呀,这床下也有鬼在闹哩!”言讫,欲探头往床下看。
月儿情兴正浓,倏的扯住,道∶“必是那耗儿闹得响哩,莫误了你我的好事!”
大郎道∶“有甚么好事?”言讫闷坐一旁。
月儿道∶“公子怎说不是好事?”
大郎道∶“我且问你,你那物儿是何人占的先?”
月儿道∶“不可说。”
大郎道∶“你当你是佛哩,还不可说!”
月儿急道∶“真的不可说!说出恐公子怪罪!”
大郎道∶“只怪那破你身的畜牲!”
月儿道∶“公子不可骂!”
大郎道∶“却也奇了!你那奸夫还不许我骂么?”
月儿道∶“不可,他是你的亲人?”
大郎道∶“亲人?可是我的亲爹不成?”
月儿道∶“虽不是公子的亲爹,恐也不远矣!”
大郎焦燥,道∶“休要与我搬弄字眼,快说你那奸夫是何人。”
月儿道∶“公子屈杀奴家了,奴家何曾愿?”
大郎道∶“即不,还不把那畜牲说出!”
月儿道∶“委实说不得。”
大郎怒道∶“再不说,拉你去见姨母,问你个通奸大罪!”
月儿慌道∶“公子且莫孟浪,倘传扬出去,合府上下,俱都不好看哩!”
大郎道∶“一个奸案,会令上下不安,我却不信。”言讫,扯那月儿欲下床。
月儿陡的掉了泪儿,道∶“乞公子饶奴家一命!”大郎一见他哭,心中更是疑惑,遂缓言慰道∶“你且说出,有本公子替你做主就是。”
月儿道∶“待公子先饶怒了奴家,方才实情相告。”
大郎道∶“且饶你就是。快些讲来罢!”
月儿道∶“是公子姨丈所为。”未等月儿往下说,那柜中床下又是一阵乱响。
大郎顾了一回,道∶“这耗儿俱都听得惊哩!”又扯了月儿道∶“是我那姨丈!我却不信,分明是你诬他!”
月儿哭道∶“奴家若谎说,愿遭雷诛火烧而死!”言讫,趴于床上号啕不止。
大郎楞怔,忖道∶“我那姨丈倒风流哩!不知这府中的丫头被他上手多少!”一头想一头去搀那月儿道∶“木已成舟,哭也无用。将此事忘了即是。”
月儿止住哭声,抬头道∶“公子不怪,奴家感恩非浅!”一头说一头做揖。
大郎止住道∶“莫要乱行礼。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且莫传扬出去,记否?”言讫替那月儿揩那泪珠儿。
月儿旋哭旋点头不止。大郎复将他覆于身下,把手去抚那乳儿牝儿,忖道∶“姨丈干得,我更干得,只可恨被那老杀才抢了先。”
旋思旋又将尘柄扶住,去那牝上移摩。
月儿紧搂其颈,低低的娇叫,把个腿儿启得更开,刹时淫水波溢滔滔,淫情大动,扭臀摆乳,候那大郎来入。
大郎磨荡了一回,腿儿一蹬,那尘柄又唧的一声入进。紧凑的抽送了百来度,再看那月儿,泪脸儿愈发的楚楚可怜,咬了香唇,耸臀顶乳,口中呀呀的叫。
大郎趴于月儿肚上大干,心中甚是气恼,直将一腔怒火贯入尘柄,把月儿的花房权当做出气筒儿,一口气入了上千度不曾停歇,入得月儿气喘不匀,张口闭目,下面淫水响得似那一片蛙声。
大郎一头干一头暗恨不已,复推起月儿双股,去跪于床,照准那肥油油水漫漫的花房刺射不休,又听那柜中一阵乱响,斜眼望去,那柜儿似在摇动,忖道∶“这耗儿也添我恼哩!”也不去顾,依旧埋头苦干。
正唧唧溜溜的抽,那床下又一片连响,敲鼓一般。又忖道∶“难道这耗儿也不欲我干月儿,我偏要干,非将那老杀才的气出够不可!”
依旧乒乒乓乓的干。那月儿着实受用,端了自己双乳浪叫喧天。
暂且不题大郎与月儿之事。先说那柜中的三郎儿。
那三郎知大郎携了月儿回来,心中欢喜,皆因二郎留那菊儿不用,白白的欲送进柜来,遂张着手儿相迎,恨那菊儿替二郎取东搬西,猛地里听那房门响亮,知是大郎闯进屋来,遂不顾许多,早将门儿大开,那菊儿恰至柜前,见门自开,唬得两眼发直,未及叫出声来,早被三郎探手拉进,反手扣了门。
那菊儿以为真是有鬼,唬得体似筛糠,三郎紧搂软月温香就亲,那菊儿又欲叫,三郎忙把舌儿度于他口中,唬得菊儿说不出话来。旋又拽出,低声道∶“莫怕!我是萧三郎!”旋又把舌儿吐入。
那菊儿知他是萧家三郎,遂放了心。却被他赤身紧搂,不免羞怯,争挣猛摔,那三郎紧紧箍住,含糊道∶“莫闹,外面听见,都不好看哩。”
那菊儿又挣,三郎复将指儿挖他那牝,刹那之间,菊儿似中了魔法,再也不拒,任那三郎轻薄。
三郎大喜,挖个织布穿梭,那菊儿竟搂了他的颈儿,把腿儿一夹一放。三郎候那淫水漫流,方才扶了尘柄,只一抬,遂滑入牝内,弄的叱的一声响,那菊儿臀儿一耸,三郎倒抵柜板,惊了外面的大郎。听到月儿言是耗儿,三郎与菊儿偷笑。听那二人入港,这二人又搂抱你迎我凑大弄了一阵。及闻那大郎月儿不是处女身儿而争,二人才歇了一回。及闻月儿那奸夫是姨丈大人,二人忍不住又一遍狂干,弄得柜儿又响。
三郎一头干一头忖道∶“我那大兄长比二兄长明理多哩,是破罐子干得更凶。”
思想乐处,不禁将那菊儿肥臀一捞,令其腿儿倒控腰际,入个满满足足,那柜儿自然合着东倒西歪。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惊看羽箭彼此欢欢
诗曰∶
莲幕吐奇筹,功成步武侯。
庸人消反侧,北阙奏勋猷。
且说萧家客房内,明火热仗于床上云翻雨狂的是大郎与月儿,柜中立着交欢的是三郎与菊儿,独独苦了床下的二郎,耳闻淫声浪语,却不敢动,只将个硬直直的尘柄拿床板出火,那大郎与月儿上床伊始,二郎即将腰中的棒槌当做了鼓槌,先是一击,后听那床上的人儿干得闹热,愈发的猛敲,险将那床板顶个窟窿,及听那月儿也是被姨丈所污,不由暗恨暗悔一回。
忖道∶“这府中恐再无有干净的女子哩,不如早将那菊儿入上一阵,与大郎一般,泄那心中之怒。”又转忖道∶“趁他二人干得欢,何不潜至柜中与那菊儿取乐?”
方欲动,恰逢那大郎探头来看究竟,遂将身滚至里面,气也不敢大出,及听二人复又干起,方才睡正,只是那鼓槌儿紧一阵慢一阵的敲。
又听那柜中乱响,不禁忖道∶“我有这棒槌敲这床板,那菊儿又用何物敲那柜儿。”
心中疑惑,却又不能动,只得耐心等那床上二人干得疲了,再去柜中看个究竟。
正闭目静听,猛地里觉那床板从头动至尾一阵乱摇响,又听那月儿哭音道∶“啊呀,我欲来哩!”
又听那大郎道∶“干了这般时候,你也该来哩。”
月儿道∶“再猛速深入一回,我即来哩!”
大郎道∶“我已竭力矣!你若再不来,我即来哩!”
月儿道∶“求公子缓些。”
大郎道∶“又要我猛速,又要我缓些,究竟何为?”言讫,撑住不动。
那月儿道∶“我也不知哩!”
大郎道∶“你这妮子!入得我晕哩!我且问你,是我在入你,还是我那姨丈入你?”
月儿道∶“自然是公子在入我。”
大郎道∶“我与那老杀才哪个济事?”
月儿道∶“自然是公子济事。求公子莫忘了人。”言讫,将那脚儿点得床板答答的响。
大郎又风风火火大入了一阵,道∶“可曾来么?”
月儿道∶“你一提那老杀才,我又来不了哩!”
大郎道∶“为何?”言讫又止住不弄。
月儿道∶“当初他弄得我痛得恶心哩。”
大郎道∶“我入得不令你恶心么?”
月儿道∶“公子入得妙!”
大郎道∶“如何妙法?”
月儿道∶“非但不痛,反而爽哩,自出娘肚皮儿,未遇此快乐。公子又忘了入奴家哩。”
那大郎一头又入一头道∶“今日我入得你爽,日后你还要日日想哩!”
月儿道∶“自然,只是今日至乐,不知何日又能尽欢。”
大郎道∶“这有何难,逢你痒时,去寻我那姨丈即是。”
月儿高叫道∶“啊呀。公子一提起他,我欲来,又来不了哩!”
大郎道∶“你可恨他?”
月儿道∶“自然恨他!”
大郎道∶“你可爱我?”
月儿道∶“自然爱你!”
大郎道∶“二者皆不许!”
月儿道∶“却是为何?”
大郎道∶“他是我的姨丈,你的主人,我更是富家子弟。”
月儿泣道∶“罢罢,只怨我命苦!不与公子耍子,我回去罢。”言讫,争挣。
大郎道∶“我且不起身,看你何处去?”
月儿道∶“莫要歪缠!”
大郎道∶“今日你是走不脱哩!”
月儿道∶“留我干甚?”
大郎道∶“留你干事!我令你生不得死不得!”言讫翻天动地的干。
那月儿又哭又叫,几欲将个床儿拆断,唬得二郎于床下急急的祷。又听了一回,那月儿不复哭,只是浪浪的叫,谙了滋味,遂暗骂道∶“这贱妮子!”
又听那柜中一阵响,又是一阵溜溜的响,不禁忖道∶“那里面的耗儿溺尿不成,弄得这般水响?”正乱思,头上又是轰然大作。
就听那月儿道∶“啊呀,公子,你还是爱我哩!”
大郎又道∶“何知我还是爱你哩!”
月儿道∶“不爱我,你那宝贝缘何这般硬挺,且坚久不泄?”
大郎道∶“我爱死你哩,我的宝贝更是爱死你哩。”
月儿叹道∶“我知公子心意,能讨些公子的风流水儿已是三生修来的福份哩!”
大郎道∶“莫说风流话儿。倘你有意,日后收你做个偏房罢!”
月儿道∶“公子的话儿可当真?”
大郎道∶“且看你的心意如何?”
月儿道∶“我晓得公子之意,请公子下来睡好。”
大郎道∶“却也乖巧,待我入上一回再动。”言讫,又是阵翻江倒海的大弄。
就听那月儿大叫道∶“啊呀,公子莫歇,我来哩!”言讫,臀儿击得床板山响。那二郎于下坚柄也挺得钻天燕子一般,卜卜乱抖。
那大郎道∶“哪呀,我也来哩。”言讫,那脚儿敲得床板也闹响。二人哼叫连连,急凑凑的丢至一处。
那二郎也被激得尘柄一抖,龟头一阵乱点,竟把阳精冲出。
待那床上稍稳,二郎抹了馀精,暗骂一句,斜身欲出,去柜中寻那菊儿杀尽馀火。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佳人大闹春屋增色
诗曰∶
襦 歌米蓦,旌旄卷素秋。
笑谈铜柱立,百世看鸿流。
且说大郎与那月儿各自将那阳精合阴精丢个欢欢,激得床下潜藏的二郎情欲难禁,也把阳精泄出,淋了床板一片。杀了三分欲火,待头上床板那二人不复再动,方才急整衣襟,欲去那柜儿中寻那菊儿做耍。
方斜探出头,不意那床板又摇,只听大郎道∶“缘何我这物件儿又硬梆梆的哩!速速跪下,令我再杀上一回。”
又听那月儿道∶“我已来不起了,辜且饶上一回罢!”
大郎道∶“休要罗噪,速速跪来!你的身下置这枕儿帮衬,岂不受用?”
月儿道∶“如此还使得。”
又是一阵唧唧的响,之后又听秃的一声水响,二郎暗笑道∶“这兄长倒是战不倒哩。”又听得一阵乒乒乓乓的大弄。月儿呀呀叫得狠。
大郎道∶“可曾来得起么?”
月儿道∶“来得起哩!只是捣不到花心上!”
大郎道∶“方才你言说来不起,我便不敢发力,你且趴稳床褥,承我入来!”
月儿道∶“不信你能将我入至地上!”
大郎道∶“却也难说。”一头说一头猛干。
约有半刻,那月儿浪叫难安,惹得床下的二郎又如火砖上的蚁子一般,那话儿早已敲得床板乱响!
正心焚难当间,猛地里听那大郎吼道∶“看我不入你至地!”馀音末了,又听那月儿啊呀声轰然至地。那飞起的金莲早将桌上灯儿扫倒,霎时一片黑暗。
大郎急叫道∶“啊呀,我又泄哩!你却败阵而逃。”
就听一阵溺尿般的声儿响,泄了一气,颓然而倒,也不去顾那月儿。
那月儿摔得难过,不住的叫痛。二郎惊了一回,见灯儿骤灭,又听那月儿哼声不过咫尺,遂色胆大壮,斜身探手去扯那月儿。
那月儿只当是大郎来扶,也不多问,只管扑着腿儿,啊呀的叫。二郎搿住他的双腿,只一纵便上了身,早将尘柄扶住顺那淫水往上一溯,秃的一声连根没进,没 没脑的一阵乱叠乱入。
那月儿黑暗之中不辨真伪,被二郎这一番狠命的入,淫火又炽,腿儿倒控二郎腰上,勾了颈儿,耸臀帮衬。
二郎登觉这月儿那穴儿生得有趣,淫水汪汪不断,尘柄浸于里面直泡得趐散,遂一鼓作气入了二千馀度,直入得月儿心肝肉麻的又叫,把个腿儿朝天乱舞。
二郎复又架起金莲,那尘柄分花瓣又刺,霉时又是五百馀度。龟头被那月儿穴儿紧咬一般,熬不起,遂扪了月儿趐乳,腿儿蹬了几蹬,那道精儿滑都都滚将出来。激得月儿又是一番亲爹祖宗的叫,也将那阴精一抛而出,二人滚的闹热,险将床儿绊倒。那边厢柜儿也合着响。
那大郎正浅睡,听那桌儿柜儿乱响,遂把手向床上一摸,那还有月儿?
问道∶“月儿,莫非我真的将你入至地上不成?”
这一问,月儿惊得肉紧,忙把二郎推开,方欲发喊,早被二郎把个舌儿度得满满当当,喘了口气,低低道∶“莫怕,我是萧二郎。”
月儿听他说是二郎方才不动,半惊半喜。欲搂还羞。二郎那话儿还歇在牝户里面,未曾撤出,趁势抽了几抽,月儿又夹弄了一番,又直硬如杵。
二郎端了月儿脸,依旧将舌儿度入他的口中,深刺了一回,下面自然又是一阵唧唧的响。
大郎又问道∶“月儿,你于地上做甚?”
二郎急抽了舌儿,那月儿倒也机灵,道∶“我在溺尿哩!”二郎抽送得更欢。
大郎道∶“不象哩!溺尿不是恁般的响哩!”
月儿道∶“我这穴儿生得窄小,故如此般的溺法。”
大郎又听那柜儿也是唧唧的响,遂问道∶“你于何处尿哩?”
月儿道∶“我于地上尿哩!”
大郎道∶“缘何那柜儿里面也唧唧的响。”
月儿道∶“我且听上一回,许是你听错了。”
言讫,不令那二郎火急般的干,二人侧耳细听了一回。
果然柜儿一阵唧唧的响。
月儿道∶“许是里面耗儿溺尿哩!”
大郎道∶“那耗儿岂有你那一指长的穴儿,弄出多少水来如此的响?
待我点灯看上一回。”
月儿急道∶“我这就上床哩,点灯做甚?”
一头说一头去摸那地上的灯盏。
二郎听他二人一番言语早惊,爬将起来,欲抽出尘柄,不意那月儿贪这一段黑灯瞎火的风流,竟扯住不放。唧唧浓浓的,捉鱼一般。
二郎忖道∶“那柜中分明藏的是菊儿,他一人怎弄得如此的响亮,分明是男女交媾之声,不知那男子是谁?莫非是那鬼精灵三郎?这般时候,他早该归了,倘是他岂不气杀,自己弄来的女子倒叫他享用一番。”
按揍不住心头怒火,遂欲去那柜中捉奸。
月儿早将他卵袋扯住,二郎焦躁,月儿咬他耳道∶“你还敢乱动,那大郎欲下床哩。”
二郎这才止住,忖道∶“倘让那大郎捉住,又不好看,他的女子被我奸,却也讨了一回便宜。”
正思间,听那柜中愈发的水响潺潺,舌儿吞吐得溜溜的,好不闹热。
大郎道∶“月儿还不上床,等甚?”
月儿慌道∶“我还未溺完哩!”
言讫扯那二郎尘柄往穴里就刺。二郎咬牙一顶,早透玉门关,一阵浪浪的抽,霎时一千余度。那月儿做那忍小便的模样,只是哼哼的叫,牝中紧锁,那二郎把持不住,阳精一泄入注,遍洒月儿花心,啊呀的一叫,又丢了身子。
大郎道∶“溺尿也这般爽哩。”
月儿道∶“何曾爽,只是肚儿不涨罢了。”
言讫,令那二郎扶他上床。
二郎焉能舍得,手又不止,通身摸遍。月儿又低道∶“待我上床侧卧,将臀儿与你就是。”
大郎道∶“你与哪个说话。”
月儿道∶“我是在说梦话哩!”
一头说,一头二郎将月儿捞起,轻移脚步,将月儿置上床。复蹲倒身子,抚摩月儿的臀儿。
那月儿自将臀儿向外一耸,大郎把手一摸月儿腰身,道∶“何不睡正。”
月儿道∶“甚是疲累,待我你做个比目鱼耍子罢。”
大郎道∶“使得。”
言讫,侧睡,贴了月儿身儿,去抚那话儿,却软郎郎当的不硬。月儿道∶“这比目鱼如何做得?”
地下的二郎那话儿却早涨发发的,抚准月儿那穴儿欲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许私约奴女遂心
诗曰∶
夙昔盟言誓漆胶,谁知贪血溅蓬蒿。
堪伤见利多忘义,一旦真成生死交。
且说月儿被那二郎抱上床,月儿欲与大郎弄个比目鱼手段,奈何大郎那话儿倒也痿顿,生将个滑嫩嫩的身儿舍了,心又不甘,只好双手端了月儿双乳,摩抚不已。
月儿淫兴又举,将那臀儿耸出床外,二郎把手一摸,那话儿直矗矗乱抖,知大郎贪月儿那双好乳,遂偷将手儿去挖那牝户,那淫水一发的直流下来,打湿二郎脚儿。月儿又不住的叫,反手又捻那二郎的尘柄往牝户里塞,口里叫那大郎道∶“大郎,我喜你吃我的奶儿。”
那大郎遂小猪吃奶一般乱拱,陋得喷喷的响。
二郎知大郎忙得难顾,遂立起身形,把尘柄扶住,剥开月儿牝户,只一顶便连根溯进去了,来来往往的徐徐一阵抽插,不敢大弄出声,倒也落得一个“偷”字的快乐。
月儿被两个男子入弄,更是兴动情狂,令那大郎将双乳端紧,乳头儿并做一处,吞于口中,不容他丝毫有懈,直陋得乳儿蓬蓬,下面愈发的奇痒,遂反手帮衬二郎臀儿猛掀死扣。
二郎扛了他的一只腿儿,斜刺里大弄。自然少不了乒乓的响。那大郎收了口儿道∶“缘何你那臀儿乱响哩!”
月儿道∶“啊呀是蚊儿忒多,咬得我紧哩!我便拍这该死的蚊儿。”
一头说一头于二郎臀上猛击。打得二郎愈发的火动,那尘柄舞得风生水响。时又听那柜中水声更响,二郎知那菊儿也正在好处,遂磨想月儿又是那菊儿,深抽浅送干了一回。
月儿被入得又至紧要之时,把个臀儿耸迎不止,那乳头儿自然离了大郎口儿,大郎去撮那乳儿即离得远,又听那月儿高声的叫,似与人交欢至妙处样儿,不免生疑,把手急探月儿腿间,方至莲瓣,登觉–物于其中来往冲突,不禁大怒,欲喝骂,又暂息怒火,忖道∶“捉奸捉双,待我将其抱住,看这奸夫淫妇如何说法。”思此,急收了手儿,欠身张臂去扑。
那二郎正干得狂逸,一时忘了大郎在彼。那月儿也淫情甚炽,哪顾许多,二人正刀架颈上也分开不得,堪堪欲至佳境,大郎忿忿,猛地里斜趴而至,拦腰抱住二郎,身下死死复住月儿,大叫道∶“奸夫淫妇干得好事。”
一声大吼,唬得二郎与月儿心胆俱裂,只止不住的对丢了一回,三人扭做一处,挣了几挣,一发的滚至地上。那大郎却不放手,急得二郎与月儿通身是汗,正无计间,猛地里听那柜中喊成一片,那柜儿栽了几栽,扑然而倒,险将地上三人覆个正着。
只听柜里有人叫道∶“二位兄长快来救我。”
又有人叫∶“月儿姐姐救我来。”
三人楞住,良久,大郎方才呵呵笑道∶“如今谁也脱不了干系了,大家起身罢,救人要紧。”
言讫,放了手儿,去寻那灯盏点上,三人互看俱都是赤精条条的。月儿害羞,欲去着裤儿。
大郎道∶“干都干了,还害的甚羞?还不帮抬柜儿。”
二郎也讪讪的一笑,去扳那柜儿。
三人合力,将柜儿翻转,打开柜门,先将三郎扯出,月儿又将菊儿抱出。那菊儿把手遮了脸儿,不敢去看那二郎。
二郎道∶“如今还害羞哩!我兄弟三人是一家人,你姐妹二人也是一家人,二家人合成一家人,岂不也妙哉?”言讫把眼光去相那大郎。
大郎忖了村道∶“不如趁此良宵,我等五人弄个联床大会尽欢如何?”
三郎道∶“甚妙!甚妙。”言讫,去相那月儿忖道∶“这妮子骚得难得,上了他的身儿更乐。”
大郎道∶“却也有一件不公!”
二郎道∶“正是。”
三郎道∶“何事不公?”
大郎道∶“我二人俱都带回了女子受用,独你无有,还拣了许多便宜。”
三郎道∶“二位兄长何必与小弟计较,待我与表妹成亲之后,定令二位兄长乐上–回。”
大郎惊道∶“莫非你已上手?”
二郎道∶“说话算数?”
三郎微笑道∶“有道是妻子如衣裳,何足惜哉。”
大郎二郎欢喜道∶“如此说来即公理!”
言讫令大家将床儿俱连在一处,五人上床睡了。
那二郎搂了菊儿挺尘柄即刺,三郎也抢了月儿上马即战。
大郎看得呆,道∶“我又寻那个干哩!”
二郎道∶“寻表妹去干。”
大郎道∶“也是。”
三郎道∶“看姨母不打死你。”
大郎道∶“表妹干不成,权且将菊儿让与我罢!”
那二郎与菊儿干得正紧,齐声道∶“不可。”
大郎道∶“菊儿弄那倒浇蜡烛,把那后庭让与我罢。”
那菊儿也乐得让两个男子侍弄,遂令二郎仰卧,照准尘柄桩下,覆于二郎身上,将那臀儿耸起,大郎一见,目摇神迷,复立于其臀后,扶了尘柄刺那后庭。那菊儿害痛,二郎于下便给他些好处,倒弄了几回,又抹些淫水,搠进了大半根,后又一发的顶了进去,入得菊儿欲仙欲死。
三郎见他三人干得起兴,愈发的将月儿干得骚态百出,又效那大郎样儿,入得月儿后庭,自然又是一番奇乐。折腾了一个时辰,三兄弟轮番上阵,二姐妹依次应敌。你哼我弄,喷喷之声彻夜不止,俱都将异味尝遍,直至鸡鸣,方才顺眠倒卧而睡。不题。
且说小姐被夫人叫去非为别事,乃是一番闺中训导。那萧氏知自己的三个甥儿生性风流,遂告诫云仙莫与他等孟浪。那云仙含羞不答,点头称是。
见天色黑暗,萧氏亲自送云仙归房,也合该事发,点上灯盏,萧氏见那床上血迹狼籍,登时大怒,喝令云仙招来。
云仙暗恨做事慌乱,严令之下,早已下跪尘埃。萧氏一见,油煎肺腑,泪如雨下。云仙大惧,缄口不言。
半晌,萧氏方才缓声问道是何人所为,再三相诘,云仙只得招了是那三郎。萧氏长叹一声,道了句命该如此,遂令云仙立起,道∶“再过两载,即将你配于那三郎。”
云仙心中欢喜,连道不孝,哄走了萧氏。
翌日,萧氏差人叫来三郎诘问。三郎知与云仙事发,叩头不已。萧氏又叹了一回,道∶“归去后与你父母言明,再过两春,择了吉日来娶云仙。”
三郎方悬心解释,揩了一头汗水,当下兄弟三人被逐出萧府。三郎偷个空当自然与那小姐又绸缪了一回,不须繁絮。
却说兄弟三人出了萧府。大郎合二郎叹道∶“又要等上二年,如何等得?”
三郎道∶“何不将菊儿月儿带回。”
二人苦脸道∶“恁般的话还不将我二人打死。”
又道∶“云仙过门之日,莫忘了让我二人乐上一回。”
三郎道∶“这个自然。”
又道∶“隔些日子,又是姨父大人生辰,我三人又以拜寿为名来此乐上一回。”
二人齐道∶“三弟真乃诸葛也。”
三郎道∶“届时将这府中的丫头俱都淫遍。”
大郎道∶“可否令我二人通上表妹一回。”
三郎道∶“二春已后方可。”
二人齐道∶“倘先令我二人通那云仙一回,纵然为你当牛做马俱可。”
三郎道∶“二位兄长何必如此说,届时自会替二位兄长寻个方便。”
二人大喜,前后将个三郎捧着走。
三郎道∶“日后倘有嫩货儿,定先让我先尝。”
二人虽心中不悦,口上却说∶“这个自然。”
说话间不觉已行了十馀里。抵暮方归,三人叩见了父母,将拜寿一事细说。惟未将风流事儿露出丝毫。
自此,兄弟三人盼那萧府拜寿贺春,更盼那二春之后迎娶云仙的日子。心中愈发的长了草般,狗马声色,掷废光阴。后事不知也知。正是∶怡怡常自淫人痴,书曰忙忙尽所思;
月貌花颜容易减,偎红倚翠莫交迟。
且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
有限时光休错过,等闲虚度少年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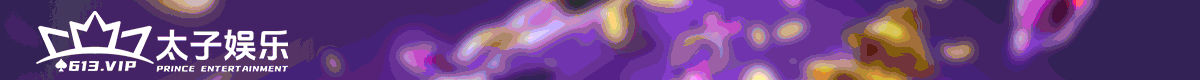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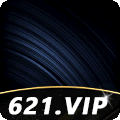






 星河电子
星河电子 星宇电子
星宇电子